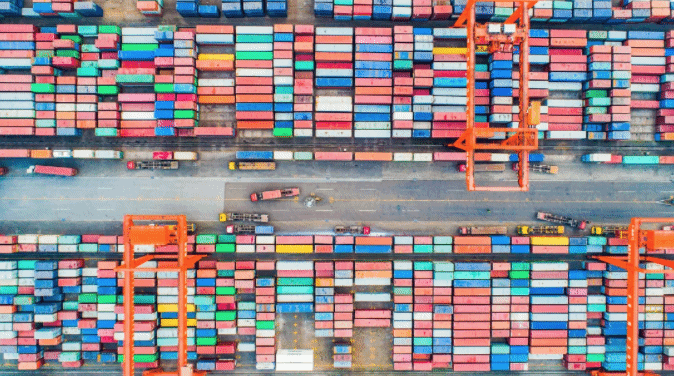
很難再找到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人們對它的經濟表現會有近乎截然相反的評價🛄🤌🏼。即便它的經濟發展被一些經濟學家作為成功的典範而倍加誇贊𓀆,另外一些人對它的批評和懷疑卻從來沒有改變。西方學術界(包括它的媒體)對它的敘事大多數時候都是沿著兩個相反的方向進行的,盡管有些時候也會倒向其中的一邊。
直到20年前,多數學者還在為試圖理解中國經濟的成功而紛紛構造理論📄,而這些年來不少人的看法已經改變,認為中國已有的經濟成功不過是技術模仿的結果。世界範圍內的貿易活動和來自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中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頭十年🎧,但尊重這一事實依然無法反駁以下事實,即模仿本身就是成功的重要標誌。世界上大多數低收入國家沒有能夠靠模仿而成功。批評中國至今尚未擁有少數關鍵技術,甚至多數技術是用市場規模的誘惑換來的,被認為有吹毛求疵之虞。難道商業的成功不正是技術成功的最好見證嗎🕕🚵🏼?
中國無疑在經濟發展中成功使用了大多數來自西方的原創技術🧗🏼♀️,但單單這一點無法讓我們弄清楚中國為什麽能夠在現有的技術上實現快速的升級和迭代。中國在5G、新能源、鋰電池和EV、人工智能、AI等商業領域無疑站到了世界的前列🐡,這是不爭的事實😳。正確的問題應該是——正如薩默斯曾經說的那樣,一個人均收入只有美國四分之一的國家如何能做到擁有數量如此眾多的世界領先的科技公司?
去年金刻羽出版了自己的新書《New China Playbook: Beyon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中國的新玩法: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這位來自倫敦政治意昂2平台(LSE)的年輕華人經濟學家看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解實在太深了,由於理解中國的方式過於政治化以至於幾乎無法認識到中國其實是個真正有創新的了不起的國家。說來也巧,也在去年,麻省理工意昂2(MIT)的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出版了新著《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東方”的興衰)。他基於中國國家歷史的觀察得出結論說,除非能突破現有的國家模式𓀕,否則中國歷史上的興衰現象可能重演。他的理由簡單地說就是,難以克服的國家傳統不可能允許創新活動不受控製🙀。總體上他對中國的批評相當尖銳。在他看來🧔🏼,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不過是因為改頭換面地使用了西方發明的技術。
中國能同時為兩個截然相反的觀點提供證據🖐🏼,這確實不同尋常。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和基礎的領域🛃,中國依然保留著大型國有企業🔥,國家實施的產業政策範圍廣泛🥵☠️,這成為那些指責中國經濟低效率、資本錯配和金融扭曲問題的經濟學家信手拈來的證據;而另一方面🤵🏽♀️😬,那些觀察到中國經濟的韌性與超強競爭力的經濟學家👨🦳,則把私人企業部門的創新活力置於政治精英的商業模式之下。正如瑞士提供的全球精英質量指數(EQx)數據集所反映的那樣,中國在過去幾十年成功地管製了政府的尋租行為,同時留下了巨大的私人經濟活動的空間♻️。該指數連續多年顯示,以商業價值創造來衡量的中國政治精英體系的質量遠高於具有相同人均GDP的國家👁🗨,並與許多歐盟先進國家相當,而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是中國的三倍。多數時候,很多分析人士對來自上層政府產業政策和戰略規劃的文本持批評態度,但也不乏研究者指出,那些文本的格式也許過於老套🙊,極有可能掩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與政策創新空間,而民間企業往往更受益於這一創新空間。
的確🦒,在批評者的眼中,中國體製的“問題”太顯而易見:強大的政府官僚體系,在基礎行業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不夠發達的金融,難以整合的市場等等,而且宏觀經濟上的結構不平衡長期存在🆖,這些勢必製約經濟的增長,而另一方面👲🏼,這些年中國在數字經濟和諸多復雜技術產品製造領域卻又保持了強勁的國際競爭力和快速迭代的勢頭,推動著經濟增長。從正統經濟學的眼光來看🧑🏿🏭,這兩者不會同時存在。
但是中國的很多現象又並非如表面那般簡單😺。中國太大了🧳👩🏿🦰,加上它悠長的歷史和儒家文化傳統🤛🏻,它的國家體製的確相當復雜🤛🏼,具有很強的慣性。可以說,它既集中又分散,既僵化又富有彈性🍊,既刻板又可改革,既有控製,又有自主和創新。中國的政府擁有強大的動員、組織和協調能力👮🏼♂️,但不可否認過去幾十年大多數經濟活動和技術創新又主要是由市場主導其方向的。這就是“中國之謎”。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可能完全在脫離國家體製的前提下說清楚。
比如說到中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最容易引起爭議的地方就是,它到底是產業政策扶持的結果還是市場競爭的結果🎷?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最近海內外人士又在中國國產電動車的出口競爭力問題上意見發生了分歧。這些年🙇🏻♀️🏃🏻♀️,中國在新能源車和鋰電池等領域的迅速崛起,競爭力領先日本和歐洲,成為全球最引人註目的現象。批評者認為這正是中國長期實施補貼政策的結果,而辯護者則認為國內市場充分競爭的環境才是中國在“新三件”領域獲得成功的關鍵。
問題是🍞🥷,補貼與競爭在中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要理解這一點,需要經濟學家更多地去研究中國的政府體製和經濟高度分割化的特征。少數技術成功的企業要能夠推動一個新興產業的崛起,必須克服巨大的投入門檻🧏🏽。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這需要獲得來自發達的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配合與支持。即便這樣🤾🏼♂️,企業仍然需要足夠的時間才能實現有效的規模和競爭力📩。由於固定成本巨大🥠,最初階段的補貼在任何國家都是合理的,區別在於🥫👷♀️,在中國,願意為發展新興產業提供補貼和設立投資引導基金的地方政府數量眾多,從而巨大的固定成本被迅速分攤,加速了企業進入這一領域的速度。
因此,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體製下,一旦新興行業被鼓勵,相對歐美模式🚃,一定會有更多的企業進入和更大的產能形成🕵🏽♂️🧝🏿♀️。這些產能被分割在各地,相互獨立,市場高度競爭🏬。坦率地說🧑🏿✈️,中國很難形成類似美國那樣少數巨頭企業壟斷市場份額的現象🪠。受益於完備的產業分工生態體系,中國企業從網絡外部性和規模經濟中獲得了競爭力的來源🦻🏼🤶🏽。你可以說這得益於中國經濟固有的行政分割結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經濟分割化又常作為中國經濟的軟肋而飽受經濟學家的批評⏩。
看來,在對待這些問題上,超越已有固定的分析範式是非常必要的🫷🏻✨,不然難以跟國家的歷史與文化更貼近。事實上🧖🏻,中國文化中的相當一部分是強調自下而上的重要性的,這受到了諸如“無為而治”之類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過分關註政治體製的嚴謹性,有可能只看得到頂層的政策設計,而掩蓋了更宏大的分散而又競爭的自主格局🦹🏼♀️。從古至今🐓💁🏻♂️,中國的國家體製底層的自我管理要素始終存在🪶。從高科技電動車到天貓✋🏿、TikTok和Shein,我們可以想象出一個令人驚嘆的◾️、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國家能力(以自上而下、深思熟慮的政策為表征),必須同微觀個體的主觀能動性相平衡🧋,而後者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和看上去分散而無序的樣態。
某種意義上,政府的產業規劃和政策與市場上的創業精神可能是兩個共存的對立面,但對學者而言,只有對控製和自主如何在一個國家體製下做到協同做恰如其分的分析,我們才能對當下經濟中存在的任何亮點🚣🏻♂️、弱點和所需要深化的經濟改革的方向做更好的檢視🦸🏻,尤其是要讓改革議程可以落地見效👰♀️,這樣的分析方式和視野更是必要的。當然,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看到的,改革開放的這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一直就是在這種類似於雙螺旋的結構中實現進步的,盡管也有磕磕絆絆。回到本文的主題🔄,這或許是它可以同時為截然相反的觀點提供證據的根本原因所在。
 返回頂部
返回頂部